在娇弱的女子和平庸的男子夹缝中求得生存,在事业中争得女性的社会价值,一些知识分子女性们,选择以男性的姿态面对事业与人生,在事业和生活上扮演“男子汉”的角色,这种性别气质的转换,就被称作女性的“雄化”。而张洁作品中这一类被“雄化”了的知识分子女性形象,主要是以《方舟》中的梁倩、柳泉、曹荆华为代表。
《方舟》是张洁深入开掘中国当代知识妇女内心世界的重要小说,关注的重点是女性艰难的社会处境,作者从女性实现自身价值的角度进行了更深一层的思索,堪称一部女性新生活的艰辛“创业史”。小说中的三位女主人公:荆华,理论工作者;梁倩,电影制片厂导演;柳泉,难得的翻译人才。她们的性格、经历各异,但都因为与丈夫离异或分居而住在一起。在婚姻上,她们可以说是“格外的不幸”,悬置在她们呢头顶的是男性压迫:色情的男人(对柳泉)、妄自尊大的男人(对梁倩)、思想僵化的男人(对荆华),这些都给她们重重阻碍和打击,甚至周围男性(如邻居居委会雷主任)价值评判的眼光也对她们实行精神围困。我们且不说那个毫无共同语言、动辄大打出手的柳泉丈夫,就是白复山——梁倩的丈夫,那个所谓的音乐家,在扮演假仁假义的角色时所表现出来的泰然自若,使得连见过世面的梁倩,也不得不目瞪口呆。正如柳泉所感慨的:“爱情这原是人生里极其严肃的一个课题,现在都让一些人亵渎了。”对男性,对爱情的失望,成为了女主人公们从家庭出走的一个直接原因。
如果说《爱,是不能忘记的》通过钟雨和爱的牺牲实现了女性情感人格,那么,《方舟》则通过梁倩、柳泉、荆华三位女性对男性压迫的不懈斗争,对自己事业的执着坚持的勇气,呈现了女性社会人格的坚强和自觉。荆华沉着冷静,梁倩豪爽侠性,柳泉敏感温柔。她们气质个性各异,却有最为共同的品性,即对男性压迫的抵抗,对女性人格尊严的彼此关注和维护。
构成她们对立面的男性压迫,在“女儿国”之外无处不在。压迫是形形色色的,色情、蔑视、歧视和拖延,设置了种种阻碍、关卡。压迫的目的则是共同的,即阻止她们获得社会认可、取得自身的人生和社会价值。荆华的论文引起了争鸣,刀条脸在机关主持的座谈会上用卑鄙的手段坑她;梁倩的新片不断被卡审,甚至被枪毙;柳泉为外国客人当翻译,被一再想侮辱她
然而,促使知识分子女性从家庭出走,追求自身的社会价值,寻求妇女解放的道路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的矛盾现状。“也许这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调和的矛盾,你要事业,你就得失去做女人的许多乐趣。你要享受做女人的乐趣,你就别要事业。”梁倩的这一发现,揭示了一个更为严峻的现代婚姻形式下的职业女性的两难处境。它一方面表明新时期的女性可以拒绝接受男性世界为她们设定的角色;另一方面又表明在现今条件下这种叛逆给女性带来的失望、悲哀、孤独是不可避免的。面对中国长期以来的传统观念所形成的广大牢固的男性世界,这三位女性所组成的小小方舟近似于孤军深入,驶入了孤独、困窘、无奈的境地。
如果说钟雨、曾令儿追求的是一种超世俗的精神之爱,是把希望寄托在天国,是“痛苦的理想主义者”。那么,以梁倩、柳泉、荆华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女性则为我们树立了自强自立的女性形象。张洁在塑造这一类自强自立的女性形象时,创作心态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早期对理想爱情的呼唤、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在这个阶段,已经被苦闷、怨恨、仇视以及哀伤、孤独与忧郁所代替。她曾这样说到:“多年来,我寻找,像那个所谓的笨蛋一样,不断地、徒劳无益地……而我终于明白,人是不可能讲自己的臂膀变成天鹅翅膀的。”她扔掉了之前那种对童话般理想爱情的憧憬和执着,以尖刻的言语、愤怒的心情,无情地嘲笑现实生活中种种丑陋的现象。为了和传统观念相抗争,张洁在创作中不仅将知识分子女性“雄化”,有时甚至故意夸大她们外表的“丑”,这可以说是当代女性对封建传统、对男权社会秩序的一种反叛,但在反叛的同时,她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走进了女性自我解放过程中的误区:在解决女性“怎么爱”和“怎么做”的问题上,张洁将柳泉、梁倩、荆华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女性塑造成为了雄性化的“寡妇俱乐部”的成员。她过分强调了男女之间的对抗与隔膜,而漠视了二者的和谐与理解;过分强调了一些男人的丑陋,而忽略了另一些男人的优秀。这不能不说是张洁在塑造“雄化”知识分子女性形象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缺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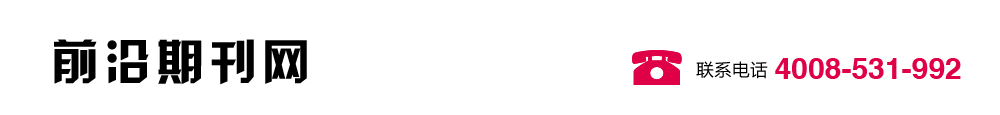


 唐编辑2113771617
唐编辑2113771617